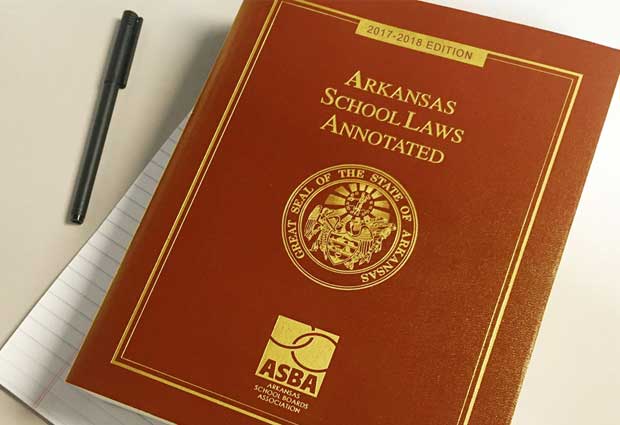全文共3423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本文首发于万邦法律
编者按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杰出常任访问学者范思深(Susan Finder)教授是著名中国司法制度研究专家,其主办的《最高人民法院观察》(Supreme People' Court Monitor )是国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了解和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窗口。6月底,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正式宣告成立。国际商事法庭及相关的对接机制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改革的一大创新举措,也引发国内外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热议。范教授近期亦撰文进行分析,其评论是目前外界此领域研究中最为深入细致的。经其同意,特进行翻译,供读者参考。作者借此机会感谢相关专家对本文写作的帮助;授权并感谢万邦仲裁翻译本文;感谢相关专家对翻译的仔细把关。
2018年6月底,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仪式,宣告了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下称国际商事法庭或CICC)。《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也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正如我今年早些时候所写的:政治和技术要求共同塑造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下文将予以详述。
一些律师事务所(包括北京中伦所和英国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已在其文章中对国际商事法庭做了总体介绍,预计还有文章会就此进行介绍,因此,本文不再对国际商事法庭进行总体介绍,而是作出若干评论。
在我看来,国际商事法庭的设计,受到了中国法律、中国法院制度的性质以及相关管理体制的制约。一些中国评论人士私下将国际商事法庭称为“迷你巡回法庭”,但国际商事法庭整合了一些创新举措以及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规定(其中一些创新迄今尚未被这些评论者认识到)。最高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司法解释规定较为简短,许多相关问题没有解答(下文会提及)。个人估计,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细则规定的出台,一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由于国际商事法庭法官人数不多,管辖权有限,这可能意味着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对“一带一路”争端解决的总体趋势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一个配备中国相关领域最博学的法官团队专门从事国际商事审判的法庭,其对中国司法机关审理国际贸易和投资案件的司法能力会有正面提升作用,特别最高院领导层知道国际法律界正关注着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情况。从近期报告来看,目前还不清楚,最高院是否会为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我作为外部观察者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持续投入将会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做法,因为单单将判决书翻译成英文就得耗时良多。
从高晓力法官今年初接受新闻采访的报道可以看出,她和其他参与起草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司法解释的同事非常清楚世界上其他国际商事法院的情况(包括已设立和设立中的)。最高院的内部智库——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对此进行了研究。
然而,尽快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政治必要性意味着,最高院受到中国现行法律现实的限制。由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违反《民事诉讼法》、《法官法》和其他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而全国人大似乎也来不及或是没有兴趣通过关于上述法律例外规定的立法,这就意味着国际商事法庭的语言不能是英语,程序法必须是中国的民事诉讼法,而法官只能是根据现行中国法律有资格担任法官的人员。
根据《规定》第2条的规定,国际商事法庭受理五种类型的案件。其中,三种案件类型是相当灵活的: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所管辖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认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获准许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其他国际商事案件。这些规定使国际商事法庭能够控制受理的案件量,因为国际商事法庭的八名法官极有可能在其相关审判庭或巡回法庭仍有在办案件,并承担了起草司法解释或类似司法指导意见的大量工作。我没有收集到高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提交最高院审理并获准许的(如读者有此方面信息,请与作者联系)。可以预见的是,高级人民法院会将手头难处理的案件移交最高院,避免被发改。
尽管《规定》第4条似乎允许从下级法院选任法官,但目前国际商事法庭任命的八名法官都是最高院法官。《规定》没有提及是否通过法官遴选委员会(目前的司法改革之一)来选任这八名国际商事法庭法官,或未来选任时是否通过法官遴选委员会。实际上,在一些下级法院中也有经验丰富的法官能够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然而,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任命法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施行员额制后可能出现的编制不足问题),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国际商事法庭法官都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这也意味着一些法官相对资历较浅。
即将成立的专家委员会(规则尚未出台)是中国法院实践的创新。与许多其他主要司法管辖区不同,中国法院没有设立用户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这可能成为向中国法院正式提交国际意见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一委员会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委员会开会的频率以及其成员对中国法院系统的熟悉程度。专家委员可选择担任调解员或在外国法问题上提供专家意见 (细节有待规则出台)。有些专家委员则可能更愿意向最高院提供一般性的意见,而不愿介入某一具体纠纷。
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国际商事法庭可允许不将证据翻译成中文,或者不要求证据公证和认证。正如我之前所写的,中国还没有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因此在中国法院诉讼中,无论是提起诉讼或外国当事人答辩时,往往需要公证和认证。目前尚不清楚国际商事法庭是否要求外国当事人委托手续的公证认证。在现行法律的限制下,国际商事法庭允许考虑当事人提交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的证据,是一种创新。公证和认证往往需要耗费时间、金钱和大量人力。另据了解,中国正在考虑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
调解、仲裁和诉讼相结合的机制是司法改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尚不清楚有哪些国际调解和仲裁机构将与国际商事法庭实现对接,也不清楚这些机构的选择标准。但从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政策文件来看,与国际商事法庭对接的是国内机构,而不是外国或大中华地区的机构。深圳国际仲裁院和香港调解中心已达成合作安排,以实现调解协议跨境执行,因此这大概是香港可以效仿的模式。
关于判决的执行,《规定》并没有增加新内容。正如我此前文章所提到的,中国法院判决在域外以及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国执行已列上最高院的议事日程。正如我之前所写,中国(最高院法官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一直在积极参加《海牙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谈判,目前已经签署《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但尚未批准。
国际商事法庭的设计者在起草时似乎参考了德国法兰克福高等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一些做法:英文起草的文件无需翻译(如当事人同意);证人可以英语方式作证;以及广泛采用视频会议或其他电子手段。
1调解和仲裁对接机制能否与中国大陆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对接?
根据中国法律,对于海外仲裁不能采取禁令、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等初步措施(临时措施)。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建立后,上述情况是否有所改变?还是需要修改现行法律?(这种可能性更大)
2国际商事法庭面临的疑难问题是否会提交至最高院审委会或其他机构讨论?
正如我大约一年前所写的,最高院采用了新的司法责任制度,规定了合议庭审理的案件交由专业法官会议或最高院审委会讨论的指导原则。那么问题来了,国际商事法庭的疑难案件由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全体讨论后是否会进一步提交最高院讨论?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已经包括跨境纠纷解决领域最为博学的几名法官(包括专门从事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最高院民四庭的庭长和副庭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节很可能会得到解决。
3国际商事法庭两个法庭是否有自己的辅助人员?是否有自己的案件受理部门?是打算给现有人手更多的工作,还是会增加人手以支持新机构运营?
国际商事法庭法官需要资源来开展工作,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协助。如果国际商事法庭成立的后果是给现有法官增加工作量,那么相关法官因工作过度而累垮也不是不可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近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下级法院法官已出现工作过度导致死亡的情况。最高院在跨境商法领域方面的一些经验丰富、学问渊博的法官已被任命为国际商事法庭法官。
国际商事法庭及其英文网站的建立,让外国研究者有机会观察中国法院如何处理和裁决商事案件,这同时也给最高院及其最能干的国际商事法院法官团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在我看来,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会影响经验丰富的国际律师为“一带一路”大型项目起草争议解决条款。由于《纽约公约》(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相应安排)的存在以及对中国仲裁机构的顾虑,许多国际律师仍会约定离岸仲裁。我个人认为,鉴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交易范围甚广,很难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相关争议解决条款目前的通行做法,也很难预测国际商事法庭将如何改变这些做法。国际商事法庭及其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为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额外选项,其是否能够成为既高效又具有成本效益,又能保持高质量的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仍需要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