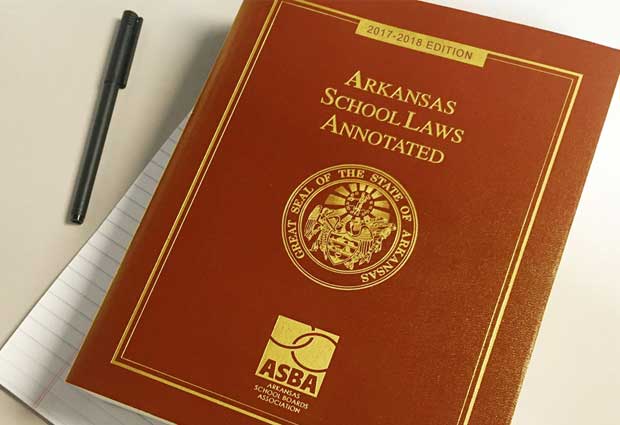全文共3445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本文来源于中国国际法前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来到著名的法国国家司法学院,并就“国内法官与国际法”这一主题和大家交流。数百年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受到众多知名法学家的关注。比如长期在波尔多大学任教的法国著名法学家狄骥,就是“国际法优先论”的积极倡导者。我们这次交流直接触及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从司法工作者的视角展开讨论,直面国内法官在国际法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今天,我打算用四个首字母为C的关键词,讲讲中国法官的工作与国际法的关系。
第一个C是Compliance,国内法官的司法活动是一国践行国际法的重要方面。遵守国际法,善意履行国际义务,既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更是中国各级法院一直坚守的理念。
在Compliance方面,我愿向大家介绍一个国际公法方面的典型案例。2005年,中国公民李先生宣布自己拥有月球,并成立公司对外售卖月球土地。中国工商管理部门认为其违背了中国加入的1967年《外空条约》,特别是其中对月球土地“不得据为己有”的规定,据此作出行政处罚。李先生不服,先后向北京基层法院和上诉法院起诉和上诉。最终,两级法院均支持了工商管理部门,判决李先生败诉。在两审判决中,基层法院和上诉法院均明确援引《外空条约》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条,强调任何国家均不能对月球主张所有权,上诉法院法官更进一步在终审判决中判定,不仅“任何国家均不能对月球主张所有权,作为国家内的公民及组织,亦无权主张月球所有权”。此案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也成为中国法官通过审判实践坚定履行本国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的范例。
第二个C是Clarification,国内法官通过其司法活动澄清有关国际法规则,对社会生活发挥更大规范指导作用。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国内法院在解释国际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特别是在适用国际条约时,国内法院的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解释条约的具体条文,在国内法与条约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还需要在条约解释方面发挥更多能动性,避免判决违背国际条约义务。
在解释国际法方面,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规定中国法院职责架构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这其中也包括对下级法院适用国际条约的问题进行Clarification。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多个司法解释,就若干国际条约问题对下级法院作出Clarification。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发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审理此类案件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具体条文存在两种以上合理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关规定相一致的,应当选择与国际条约有关规定相一致的解释。
还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从2010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对外定期发布一些经典案例,把具有共性的法律规则提炼出来,供下级法院参照执行。它们和英美法系的判例不同,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要求下级法院必须执行,但下级法院实践中一般都会参照这些案例来审理案件,因此对司法实践也有重要影响。这些指导性案例有些直接涉及对国际法的Clarification。例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8个指导性案例”,其中就涉及对《联合国国际销售货物合同公约》、《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具体条文的解释。
中国法官对国际法的Clarification态度严谨,注意征求专家意见,参考国际同行的实践。比如在2005年杨女士诉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中,中国地方法院的法官就《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29年《华沙公约》)第17条中的“损害”一词是否包括精神损害征求了专家意见;在就196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5条第2款第2项中的“公共政策”一词进行解释时,最高人民法院广泛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
第三个C是Cooperation,中国法院和法官在促进国际司法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为例,中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后,最高人民法院迅速通过发布执行通知、建立报告制度、发布司法解释等方式,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问题作出大量细化规定。中国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坚持只从程序上审查,不触及实体问题。中国法院上述工作都有效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
中国法院这种基于国际法的Cooperation精神,同样体现在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在此我很高兴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在此领域的新进展。大家知道,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通常需以条约或互惠为条件,对不存在条约关系的情况如何认定是否存在互惠,中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长期采取的判断标准是“事实互惠”,即要求对方国家有过承认或执行中国判决的先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法院的司法实践积极吸收倡议的合作精神,在认定互惠问题上逐渐向更有利于推进合作的方向转变。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沿线一些国家尚未与中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情况下,可以视情考虑实行“推定互惠”,由中国法院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这一政策还体现在2017年6月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通过的《南宁声明》中。根据声明,只要无相反证据证明外国曾有拒绝承认与执行本国判决的先例,就可以推定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这种“推定互惠”方式大大增加了认定为存在互惠的可能性,不仅对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也必将从整体上促进国际司法合作。
最后一个C是Codification,中国法官的司法实践构成了中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国家实践。《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被广泛认为是关于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论断。该款第四项规定司法判例可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虽然规约未明确司法判例是否包括国内法院的判例,但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国内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其判决可以作为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的证据,用于识别习惯国际法。此外,《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绝大部分也是由国内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归纳出来,并逐渐成为国际法的渊源之一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越来越重视对外传播本国的司法实践,许多中国法官作出的判决被翻译成外国语言。例如,2015年法国最高法院的卢维尔院长访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期间,应法方要求,中方将有关案件判决书翻译成法文供法方同事参考。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受语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法院的判例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国家实践发挥国际影响力受到了一定挑战,但中国法官的司法活动也在逐渐为构成习惯国际法证明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积累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仅介绍一个上海海事法院的案例。1936年,中国中威轮船公司将其所有的两艘轮船租给日本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使用。此后,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两轮被日本海军“扣留”,后交由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继续运营至沉没。战争结束后,中威轮船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政府索赔两轮损失,均未获赔偿。1988年12月,中威轮船公司就该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后身——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支付租金并赔偿损失。此案既是一起普通民商事案件,又涉及到与战争赔偿有关的国际法问题,十分复杂。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们将此案定性为单纯的民商事案件,将其与战争赔偿问题进行切割,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并赔偿船舶租金等费用。这项判决没有直接追究日本国家的责任,尊重了日本的国家豁免,又使战争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补偿,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国家实践。
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各国日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已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超越民族语言、文化、种族和宗教的国际语言,也深入渗透到各国国内法律制度中。未来,国内法院的法官与国际法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将更加密切,甚至超出我讲的4C范畴。但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各国的国内法官和国际法从业者都应秉持开放心态,更多从国际视角,全球维度去审视国际法和国内法,应对共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中国法律人愿秉持这样的心态,与国际同行加强交流,共同进步。
谢谢。